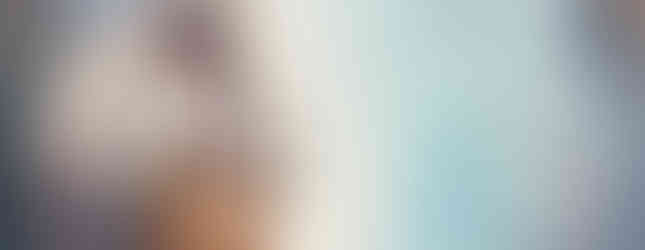不讓死亡狂傲 朱子溢
- Cherry

- Aug 2, 2025
- 6 min read
Updated: Aug 6, 2025

匆匆十小時的人生,成就了一位生死教育的委身者。
朱子溢傳道因愛兒離世,踏上教人正視死亡的旅程。談生論死十多年,他接觸多人的生命,讓基督的愛安慰傷心者的心靈,叫死亡不能狂傲。
沉重的死亡課題,他卻背得相當輕省,因為沿途有主的手攙扶着他,並肩同行。
TEXT / Cherry PHOTO / Andy
假若人生有如登上一輛列車,死亡只是一個中轉站;有些人乘坐一段悠長旅程才下車,有些人卻登車不久便要急忙轉車。
朱子溢傳道(Don)的兒子瑋恆,是屬於後者。
十小時人生 燃起祝福之火
Don的三子瑋恆在2013年出生不久夭折,為Don帶來對死亡的體會,也改變了他身為傳道人的事奉路向,投身生死教育領域。
「我和太太當然哀痛,但還是接受了事實,更要處理兩個女兒的情緒。」當時Don的長女三歲半、次女兩歲,兩個女孩子見證着媽媽的肚子一天天隆起,好不容易才與弟弟見面,轉瞬卻要說再見。
「她們已經有意識,尤其是大女受影響較深。她想起弟弟時會哭,在學校也常有特殊的表現,例如畫嬰兒車但車裏沒有嬰兒。」Don夫婦和老師都察覺孩子的情緒反應,可惜因社會支援小朋友面對死亡的資源極少,眾人想幫但束手無策;曾受教師訓練的Don和太太只好自己找資料幫助女兒們,在家庭開始親子生死教育。
「在瑋恆離世一個月後,有基督徒報紙記者知道這件事邀請我們訪問,我們便說出瑋恆的故事,讓社會知道我們的情況和挑戰。這篇報道引起一些迴響,延伸至其他報章或團體接觸我們,我們又願意公開分享,就這樣不期然踏進了生死教育範疇。」例如香港政府對24週以下夭折胎兒的遺體處置問題、道風山天使花園(流產嬰墳場)的開展工作,Don皆有參與討論。
當年Don和太太向媒體訴說決定誕下瑋恆的心路歷程,招來一些haters,Don直言非常錯愕,曾動搖是否繼續分享:「其實記者的報道寫得十分正面,可是受眾擁有不同的價值觀,甚至有些人批評得很難聽。我們沒收受甚麼好處接受訪問,純粹希望這個故事能夠祝福他人,帶來反思生命的覺醒。既然神要我們繼續做,便不再理會惡意的批評。」
人死不一定等同滅亡。瑋恆在世短短十小時,他的死化成了祝福之火,火炬從Don一家的手裏開始,至今傳遞了十多年。Don的家庭是首先被祝福的,他們毋須找專家輔導哀傷,因為受訪讓他們從多個切入點反覆梳理事件和情緒,無形中化成安慰的良藥。瑋恆也成為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的無言老師,用身體和生命教導醫學生醫術和人生的本質,造就他們日後用雙手以仁慈幫助萬人。
「許多人看瑋恆的事是災難,然而我們經歷的祝福更多。最初得悉瑋恆是『無腦兒』(anencephaly)的時候,我們不斷祈禱求神把頭蓋骨賜給他。後來回望神容讓這件事發生,祂的神蹟不是要瑋恆奇蹟長回頭蓋骨,而是要我們活着的人成為神蹟的一部分;我們這個家庭不止脫離了悲痛,甚至關係比以往更緊密。」一個親歷喪子錐心之痛的父親要說出這番領會,不容易。「我們在一切患難中,他就安慰我們,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。」(《哥林多後書》1章4節),是神的愛使Don變得強大。
連番巧合證明神同工
從全職教會傳道人轉投生死教育領域,Don與死亡課題越走越近,傳遞生死教育的受眾也越更廣泛,由病人、大學生到小朋友,都是他接觸的對象。「我既做突發的非自然死亡支援,也做家長和老師培訓。」他說。
最叫Don印象深刻的,是帶着大學生關懷一些臨終病人,還有水彩畫畫家隨行;大學生和畫家分別用文字和畫作展現病人在世最後的時光,作品會在大學、醫院、教會裏公開展覽,表揚這些病人與絕症作戰的勇氣。
「有一幅畫作名為《再生勇士》,何伯的另一半打趣提議畫家幫他加上頭盔,於是何伯就變成英勇的羅馬士兵;他也確實是再生勇士,曾經數次患癌,病到行不穩也要在街上救人。縱然他身體虛弱卻流露出屬神的盼望和積極,每一天為賺得生命而感恩。」Don介紹道。其實訪問何伯的三個月後便是展覽日,可惜他已等不及返回天家,不能與其他病友聯袂接受嘉許和親自分享人生故事。「是遺憾的,因為何伯十分期待那天。他的家人很重視這幅畫作,特別在安息禮拜上將複製的明信片送給親友。」
服事一位印尼婆婆的動人故事,也使Don深感神一直與他同工。「金杏婆婆年輕時從印尼移民香港,信主後熱心返教會。她在癌症晚期已難以再出門,告訴我們她最大的心願是返教會。」機構只能安排部分病人有義工探訪,適逢婆婆獲派義工,而且義工從事音樂製作,又剛巧曾經製作由印尼民謠翻譯成粵語的詩歌。「於是我們便帶領婆婆唱印尼家鄉的詩歌敬拜祈禱,完成了她的心願,眾人都流出感動的淚水。當天有另一位義工未信耶穌,我問他覺得接連的『巧合』是隨機還是背後有神的工作?他也一時難以回答。當然我深信唯有神才能夠作出如此巧妙的安排,讓我知道祂也參與其中。」筆者聽着Don娓娓道來,早被感動得不能言語。
死亡是不能迴避的課題
「按着定命,人人都有一死,死後且有審判。」(《希伯來書》9章27節)生與死是人的定命,也是一個普世的課題,因此Don的事奉並不受空間所限。2022年Don一家移民加拿大溫哥華,轉移到新陣地後,他繼續着手研究生死教育。
「疫情時我服事的機構重組崗位,我也從大學調職到總部做行政工作。那不是神本來呼召我的事奉崗位,讓我萌生轉換工作環境的念頭,加上我和太太一直深感小朋友在香港的學習壓力太大,希望改變生活環境,於是舉家移民。」
Don入讀神學院進修,研究「臨終神學」。入讀的神學院暫未開辦「臨終神學」這門學科,他是從「死亡神學」與「苦難神學」裏進行學術鑽研,將人觀、罪觀、生命觀等神學性討論延伸至實務性的理論而成為「臨終神學」,涵蓋人面對臨終的心理、如何處理哀傷等。
「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,對死亡各有觀點,即使信耶穌的人亦然。文化承傳是以家庭為單位,例如香港的移民家庭,下一代將會深受西方文化影響,但又受原生家庭的文化影響,而生死教育是每一個家庭不應也不能迴避的課題。在我女兒四歲的時候,她已經問我人死後是否搭電梯上天堂?瑋恆是不是在雲上?小朋友對死亡的認知比大人想像中更早。」Don的研究將從猶太人家庭傳承生死教育的文化作為探討點。
看清死亡盲點免留遺憾
相對於香港,溫哥華華人的生死教育事工起步較遲,Don看見眼前是一片片未經開墾的禾場,既代表了機會,也充斥着挑戰。
「最大的困難是我回應的心是否夠主動和創意,另一個困難是很難為生死教育事工定目標。假如目標定得過份空泛便摸不着邊際,可惜生死教育本身又沒有一個清晰的系統,需要多人合作定下具體的目標,事工的效果才能貼近人的切實需要。」他坦言在溫哥華生死教育的同路人有限,增加摸索方向的難度。是困難,然而Don早習慣迎難而上,「況且每當我面對艱難的處境時,神都會為我開路,讓我找到解決方法。」他感恩地說。
即使人沒有掩面不看死亡,也對死亡存在太多盲點,而生死教育是一面反映盲點的倒後鏡,令人看清死亡過程的底蘊。「沒錯,基督徒全清楚《聖經》告訴我們信耶穌得永生,死亡的終局是前往耶穌為我們預備的新天新地,享受永遠的福樂;而死亡的過程呢?許多基督徒都忽略了,直至人生到達臨終的階段,才驚覺當『認知』成為『真實』後,原來自己還未準備好,仍有很多東西來不及安排和完成。生死教育的作用正是提醒人們時刻儆醒為死亡作預備,減少離世時的遺憾。」
人生旅途或長或短,我們要把握光陰過得璀燦豐盛,但也不能只活在當下。始終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我們甚麼時候下車,也不是看過哪些風景,而是這輛人生列車駛向哪個終點——是否主耶穌為世人所設的永生樂土。